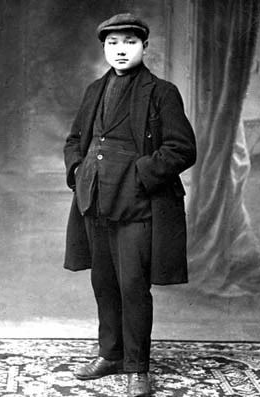
歷史是客觀的,因而不能假設。但是,如果將一位偉人從歷史長河中暫時抽離,假設其沒有發揮已然發揮的影響力,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更便于厘清偉人的功績。
對于“假如沒有鄧小平”這一問題,不同的人自然會有不同的答案。
假如沒有鄧小平,“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江澤民在追悼小平時這樣評價。
假如沒有鄧小平,“我們就不可能有房、有車,有在深圳牽手的愛”。一對來自湖南鄉下、在深圳打拼10年的新婚夫婦在小平塑像前獻花時說。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某位巨人或英雄能夠以一己之力完全改變歷史,不過,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在歷史轉折節點上,偉人的智慧、魄力能夠影響到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進程。因此,我們也試圖從這種假設出發,從個體命運、經濟改革這兩個層面,緬懷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扭轉乾坤的一代偉人。

你我命運未必如此多姿
因為他和他所作的努力,國人作為“人”的尊嚴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恢復了。

1978年:平反冤假錯案
那兩年,鄧小平繁忙的政治生活中一個經常性的活動,就是出席和主持各種追悼會,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而逝的老一輩革命家。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到1982年,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干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如此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古今中外前所未有。
人物:朱镕基(1958年錯劃為“右派”,1978年平反,1998年出任國務院總理,2003年離任)
1958年4月,在國家計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國家計委黨組報請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開除黨籍。從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作為五十五萬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農場勞動。所幸的是,朱镕基在農場只勞動了很短時間,就被調入國家計委所屬的一所中專學校擔任普通教員。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帽”,并上調國家計委機關國民經濟綜合局工作。由于朱镕基尚屬“內控人物”,他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
“文革”中期,朱镕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從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間,他所做的無非是養豬放羊,除草收割。
時至1975年,隨著鄧小平的二次復出,中國社會表現出微弱而緩慢的復蘇氣息。朱镕基回京后,又被安排至石油工業部管道局下屬單位———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朱镕基擔任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科級。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文件說,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條件已經成熟。此時,朱镕基上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
是年9月,朱镕基終于徹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并恢復了黨籍。據載,正式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國社科院組織部門的一位負責人,鄭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從他檔案里抽出來的“右派分子”材料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一言不發地看著那一張張記載著他‘反黨罪行’的字紙,在火中迅速化為灰燼”。
1998年,在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新聞發布會上,當一位美國記者問起那段“右派”歲月時,一向敢言和暢言的朱镕基表情深沉,他說: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情。

1977年:恢復高考
歷史背景:“文革”結束時,高考制度已整整廢除10年。恢復高考制度,是鄧小平復出后作出的最為偉大的決策之一。他曾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但此觀點,“文革”期間曾遭“四人幫”強烈反擊。1977年,鄧小平堅決表態要求恢復高考制度。
人物自述:張曉山(胡風之子,77級大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
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我的整個青年時代都是在極端壓抑甚至扭曲的狀態中度過的。我一度真實地感到,我不能和別人平等生活。1968年我插隊到內蒙古土默特左旗,當時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已經十余年。
1977年,我被調到塔布賽公社良種廠做技術推廣。我記得那年秋天的一天,廣播說要恢復高考了。我隱約感到這個消息跟我有關。
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資格參加,或許又要在政審的時候被卡下來。1973年、1974年這里有過兩次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機會,一次不了了之,再一次因為家庭問題被退了回來。我不敢對這次高考有太大幻想。
后來我到公社報名,居然很順利,基本上沒有什么政治上的限制。當時已經是冬天,沒有什么活,我跟公社請了假復習,整夜整夜地看書。
考試是在公社中學舉行的。我那時候也已經30歲了。考試的整個過程我都很平靜。當時還在想:即使考分夠了,能不能上也是個問題。受父親問題的影響,我對很多事情都不確定。那時父親還在獄中。
最終我未能如愿考回北京。當內蒙古師院的通知書發到我手上時,我懵了。我報的是中文專業,但卻被數學系錄取了。后來得知,學校的老師認為中文和文藝關系密切,為了避免麻煩,出于好意幫我改了志愿。
經過一番爭取,我最終進了外語系。1979年有個機會來了,當時研究生招生,在校本科生有條件的也可以報考。我選擇了中國人民大學的農業經濟專業。1982年,我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了今天。

1978年:留學
歷史背景:1977年7月,鄧小平剛一復出就主動要求主管科技和教育。他多次談話都論及科教和人才的重要性。翌年6月,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發表講話:派留學生要成千成萬地派,不要十個八個地派。要做到兩個不怕,一是不怕派出去不回來;二是不怕和人家搞到一起,這樣才能學到東西。
人物自述:裴定一(1978年中國首批公派留學生,后為廣州大學理學院院長)
1978年12月25日,我作為改革開放后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訪問學者的一員,從北京出發,途經巴黎、紐約,于次日到達華盛頓特區中國大使館。由于有中美即將建交這樣的政治背景,我們到達美國的消息在當地媒體上都有報道。
1964年我在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導師是華羅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學畢業生都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而我們這批研究生集中在當時建立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由于我們沒有去農村,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引起很多爭議。我們在這一年中經常要接受“又紅又專”的教育。一年后,也終于終止了業務學習,去了農村。1966年6月又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我離開北京,分配到大慶油田當了一名采油工,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大約一年后,隊長對我說,聽說你是學數學的,以后就擔任采油隊食堂會計吧。從此我承擔了會計和喂豬兩項任務。我在接班時,隊上僅有一頭老母豬,當我離開這個隊時,這頭老母豬已生了兩窩共14頭小豬。直到1977年底,我的工作關系才從大慶油田調到中國科學院。
得知要去美國留學,我有點不知所措,因為通知很緊急。我們首批50個人就在1978年的冬天啟程了。那一年我已經37歲,但在團里還算年輕的。
在華老的推薦下,我得以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初到普林斯頓,我感到了很大的差距。“文革”前我的數學基礎還是非常好的,如果中國沒有頻繁政治運動的十幾年耽誤,我不會差這么遠。學成兩年后,我們幾乎所有人都選擇了回國。當時只想到滿腔熱情回國報效,從來沒有想過留下來的問題。只有一個人沒有回國,但當時大家也沒有太多的反感。

1980年:上山下鄉終結
歷史背景:1977年鄧小平致信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發表重要意見。中央隨后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從此,社會各界借此開始重新思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一些探討其得失成敗的不同見解得以出現。如何從根本上解決知青問題,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
人物自述:鄧曉芒(1964年上山下鄉,返城后參加高考,現為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
在我的記憶中,1968年是我們湖南白水知青空前自由、輕松甚至充滿歡樂的一年。那一年,全國大規模的知青下放已經開始,看著那些“嫩知青”們與家人離別時抱頭痛哭的情景,我們這些“老知青”內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興,覺得這一來大家都一樣了。
那時白水的知青處于一種奇怪而矛盾的生活方式中,晚上有組織、有預謀地去糟蹋農民的菜地,白天則自發地在一起學習社論和毛主席的講話。當時知青組里有幾本磚頭厚的理論書,如《列寧選集》,梅林的《馬克思傳》,都令我望而生畏。我從那些當時出版的馬列著作單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即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開始認真地讀起來。這是我所閱讀的第一本理論性讀物。
當時勞動并不緊張,并且此時對我來說,要養活自己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著的意義只是為了能夠繼續思想。至于考大學,考研究生,連想也沒想過。
1974年,有關知青返城的一些政策出來,我到縣醫院辦了個假病歷,居然就回了長沙。我算是離開早的,1977年以后,大規模的知青返城才開始。返城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好機會,表明我可以開拓自己的命運了。而此前,在預感到自己回城無望的情況下,我早已定下自己的未來,在農村做個普通人,當然最好是一個有智慧的普通人。
回城后我就像今天的民工一樣,在城市里干最粗的活,挖馬路,建廠房。那幾年我白天扛大包,晚上讀黑格爾。1976年招工,我到了長沙市水電安裝公司。
1977年恢復高考,我受到鼓舞。第二年決定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
因為父母的“右派”問題尚未解決,我沒被錄取。第二年,我考取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這是我人生命運上的轉折點。從此以后,哲學不僅是我的愛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職業,我的謀生之道。

1992年:下海
歷史背景:蘇聯和東歐的劇變,加之中國國內的政治風波,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被推向了一個敏感而動蕩的危險地帶。當時有思潮將改革開放說成“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中國向何處去成為問題。
人物:馮侖(1984年畢業于中共中央黨校,法學碩士。曾任職于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武漢市經委和海南省委。1991年前后辭職下海,現任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
馮侖總給人一種離經叛道的味道。身為萬通地產的主席,他不說商業,卻大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他覺得有些東西實在是誤國又害人。比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的事兒,亂就亂在每個人都想管天下。他說應該糾正為“匹夫興亡,天下有責”。
他總是和自己所處的環境發生著奇怪的分裂。聽說馮侖的辦公室里盡是線裝書,他被稱為地產界的思想家,有著無數與地產無關的犀利語鋒,他裹挾著一身藝術氣質,在萬通地產通透的大廳里疾走。這是今天的馮侖。
20年前的他,是中共中央黨校最年輕的研究生。1984年于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畢業后留校任教。之后調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辦公室下屬專題研討小組,從事“文化及意識形態領導體制改革”的研究。對了,請關注微信公眾號中外人物,每天給你介紹有趣的人,有趣的魂。
1957年出生的馮侖在30歲之前,一直在正統的政治氛圍中成長并沉醉于此。1988年下半年,他又被借調入中宣部。1988年底,他被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任命為比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時被派往海南省籌建改革發展研究所,并擔任常務副所長。馮侖風云幾年,將中國最為嚴肅和核心的部門挨個兒“暢游”了一番。
可就是這樣一個諳熟中國體制規則的“紅”人,偏偏在1992年前后在海南“下海”搞起了房地產。有人戲稱,馮侖體改改到了自己頭上。
1989年風波過后,海南體改辦就解散了。當年他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團,任總裁辦主任,相當于副總裁。此時,馮侖開始重新思考自我的抱負和志向。他想知道在未來中國,工商社會是否會成為主體?
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加深了馮侖的思考。在他身后,一批批人從體制內移身商海。這些人后來被歸為“92派”,馮侖成了他們的代表人物。
作為商人,他說他現在只想讓董事會滿意。對于政治他依然抱有興趣,他說,我希望國泰民安,能讓我安安穩穩做企業。他偶然也假想當年,和大學同學張維迎拿著畢業照亂想,當年如果走仕途,“現在至少是個司長吧”。兩人大笑。
轉自每日熱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