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哲學(xué)家,而哲學(xué)家并不都是教育家。
德國(guó)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杰出代表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以宏闊廣大的時(shí)空視野,探本索原的思想方法,慎思明辨的治學(xué)態(tài)度,深入考察教育的一些核心問(wèn)題,其關(guān)于理性與精神、科學(xué)與人文、生存與歷史、自由與權(quán)威等的論述,凸顯他對(duì)教育本原的深邃思考和把脈教育病癥的睿智洞察,從而以深具哲學(xué)意蘊(yùn)的教育思想對(duì)當(dāng)代教育產(chǎn)生重大影響。
卡爾·雅斯貝爾斯生活在一個(gè)政治變革廣泛深遠(yuǎn)的時(shí)代,終其一生伴隨納粹政治起而覆亡與歐洲文明戰(zhàn)后重建的歷史進(jìn)程。1969年,他以86歲高齡逝世。1977年,從雅斯貝爾斯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赫爾曼·洪恩(Hermann Horn)輯錄其談?wù)摻逃膬?nèi)容,編纂成《什么是教育》一書(shū)并由Piper出版社出版德文本。1991年,三聯(lián)書(shū)店出版《什么是教育》的首個(gè)中譯本,收入“德國(guó)文化叢書(shū)”,譯者鄒進(jìn)。2023年,三聯(lián)書(shū)店出版童可依譯本《什么是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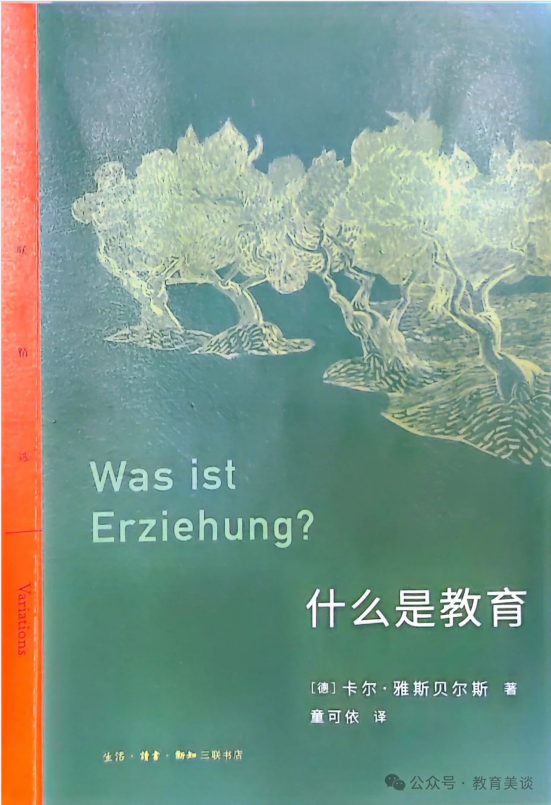
《什么是教育》是中國(guó)最具影響力的外國(guó)教育名著之一,不僅出版及印次多,印數(shù)大,而且僅從知網(wǎng)收錄的文獻(xiàn)看,對(duì)其引用達(dá)到數(shù)以千計(jì)。究其原因,在于——
《什么是教育》對(duì)教育本原問(wèn)題的剖析,激發(fā)對(duì)提升教育品質(zhì)的深度思考。
明代“心學(xué)”之集大成者王陽(yáng)明先生曰:“為學(xué)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jìn)。”知其所來(lái),方知所往。所以,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教育”這個(gè)基本問(wèn)題,從根本上決定辦學(xué)育人的理念、原則、策略與方法,影響著教育生活品質(zhì)與學(xué)生發(fā)展質(zhì)量。
在《什么是教育》這本書(shū),雅斯貝爾斯開(kāi)宗明義:“教育關(guān)系在人類此在中(因年齡、教養(yǎng)、素質(zhì)而異)不可或缺。”從“關(guān)系”這個(gè)底層邏輯出發(fā),他在不同層次、角度對(duì)教育的內(nèi)涵加以清晰、細(xì)致、具體的明確。
如,“教育是在人與人(尤其是年長(zhǎng)者與年輕一代)的交往中,通過(guò)知識(shí)內(nèi)容的傳授、生命內(nèi)涵的分享以及行為舉止的規(guī)范,將傳統(tǒng)交給年輕人,使他們?cè)谄渲谐砷L(zhǎng),舒展自由的天性。”這是在師生關(guān)系上定義教育。
如,“真正的教育不提倡死記硬背,但也不能期望每個(gè)人都成為富有真知灼見(jiàn)的思想家。”這是從教學(xué)方式與培養(yǎng)目標(biāo)的角度定義教育。
如,“教育首先是一個(gè)精神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其次才是科學(xué)獲知的過(guò)程。”這是從過(guò)程與成效的角度定義教育。
如,“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shí)和認(rèn)識(shí)的堆集。”這是在德性與知識(shí)的關(guān)系上定義教育。
如,“教育作為一種特殊行為,與訓(xùn)練、照料、控制等都不同。”這是從區(qū)分教育與非教育的角度定義教育。
諸如以上所引,雅斯貝爾斯對(duì)“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或陳述,書(shū)中在在皆是。這些判斷句或陳述句,構(gòu)成關(guān)于教育的認(rèn)知地圖。盲人瞎馬,南轅北轍,目標(biāo)落空緣于路走錯(cuò)了。反躬自省,雅斯貝爾斯這些金石之言足可為我們鏡鑒。
《什么是教育》闡述的教育概念或理念,引起對(duì)教育過(guò)程質(zhì)量的深切關(guān)注。
概念或理念是關(guān)于事物的本質(zhì)性與整體性的界定。一個(gè)人對(duì)某個(gè)概念理解得怎樣,對(duì)某個(gè)理念領(lǐng)悟得怎樣,一般地會(huì)反映在他的待人處事的態(tài)度上和行為方式上。所謂“人類的行為是思想的最佳譯員”,乃是說(shuō)概念或理念的價(jià)值。
在《什么是教育》這部書(shū)中,雅斯貝爾斯提出并闡述多個(gè)為我們耳熟能詳?shù)母拍罨蛐g(shù)語(yǔ),如“有信仰的教育”、“學(xué)校精神共同體”、“本真的教育”、“愛(ài)作為教育的根本力量”、“整體性知識(shí)”,等等。
這里,說(shuō)說(shuō)“有信仰的教育”對(duì)我們的意義。
雅斯貝爾斯說(shuō):“一切有意識(shí)的教育都以自身的實(shí)質(zhì)為前提。教育須有信仰,沒(méi)有信仰的教育不過(guò)是純粹的教學(xué)技術(shù)。應(yīng)當(dāng)認(rèn)清教育的實(shí)質(zhì)與意志,若非如此,便無(wú)法找到教育的宗旨。因此,我們時(shí)常聽(tīng)到的一些教育口號(hào)并沒(méi)有把握住教育的真正實(shí)質(zhì),諸如學(xué)習(xí)一技之長(zhǎng)、強(qiáng)健體魄、獲得國(guó)際視野、陶冶性情、確立民族意識(shí)、培養(yǎng)勇氣與自立、提升表達(dá)能力、塑造個(gè)性、創(chuàng)造共同的文化意識(shí),等等。”口號(hào)太多,心里太急,教育不可避免地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淖,實(shí)質(zhì)是缺乏持續(xù)做教育的定力。放言高論、認(rèn)識(shí)片面、跟風(fēng)搖擺、折騰不已,離教育的本質(zhì)要求只會(huì)越來(lái)越遠(yuǎn)。
所以,做教育信仰什么,就會(huì)堅(jiān)守什么,這決定著教育的品位與教育者的境界。而執(zhí)著于教育信仰,要有對(duì)教育本質(zhì)與價(jià)值的守護(hù),摒棄功利心,淡泊以自持,把學(xué)生發(fā)展置于教育的最高位置。如此,教育就會(huì)多一些生動(dòng)活潑,少一些平庸浮躁。
《什么是教育》對(duì)教育病態(tài)的批判,啟迪對(duì)教育改革之艱巨性的深刻認(rèn)知。
雅斯貝爾斯逝世已逾半個(gè)世紀(jì)。
讀《什么是教育》,我常常感嘆于他的超越歷史與時(shí)代、文化與民族的洞見(jiàn)。在本書(shū)的《第六章 依存于整體的教育》,他對(duì)已現(xiàn)危機(jī)征兆的教育狀態(tài)有一段描述:“缺乏統(tǒng)一觀念的高強(qiáng)度教學(xué)、層出不窮的文章書(shū)籍、不斷翻新的教學(xué)技巧。教師個(gè)人對(duì)教育付出的心血是前所未有的,但因?yàn)槿狈φw的支撐,卻顯得貧弱無(wú)力。而且,我們的狀況所獨(dú)有的特征似乎是:放棄實(shí)質(zhì)性的教育,卻沒(méi)完沒(méi)了地從事教學(xué)試驗(yàn),在這種教育的解體中形成了種種無(wú)關(guān)宏旨的可能性,這是一種以不真實(shí)的直接性呈現(xiàn)不可言說(shuō)之物的企圖。一種嘗試迅速替代另一種嘗試,教育的內(nèi)容、目標(biāo)與方法不斷更換。”
從這段文字,我聯(lián)想到的詞,有“焦慮”、“內(nèi)卷”、“模式”、“負(fù)擔(dān)”、“高效”等等,在這些詞的之前或之后,當(dāng)然是要加上“教育”或“教學(xué)”的。近些年來(lái),由這些詞指向的教育病態(tài)都曾吵得很熱,對(duì)這些病癥的診療方案亦推出不少,為此做了很多的事似乎也都不太令人滿意。于是,在這段話的旁邊,我寫(xiě)下“如在目前!”幾個(gè)字。
發(fā)現(xiàn)問(wèn)題才能解決問(wèn)題。
從存在主義的哲學(xué)邏輯出發(fā),雅斯貝爾斯認(rèn)為,教育的核心在于喚醒個(gè)體的存在自覺(jué),使其意識(shí)到自身的獨(dú)特性和與世界的聯(lián)系。為此,他指出:“唯有人的回歸才能實(shí)現(xiàn)真正的教育革新。”倡導(dǎo)“本真的教育”,祛除外加于教育的功利的東西,專注于學(xué)生這個(gè)“人的發(fā)展”,培養(yǎng)有獨(dú)立思考能力、有批判精神、有創(chuàng)造力的現(xiàn)代公民。
學(xué)生如此,教師更當(dāng)如此,民族的未來(lái)就在于此!
(本文來(lái)源微信公眾號(hào):教育美談,作者:姜野軍。轉(zhuǎn)載僅供學(xué)習(xí)交流,圖文如有侵權(quán),請(qǐng)來(lái)函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