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古史辨是改變近代中國史學氣候的一個晴天霹靂,值得被深入分析討論。應該聲明的是:由于筆者把古史辨運動當作近代學術思想發展中一個歷史現象來描述,所以,并未能稍稍照顧到上古史研究的專門問題。事實上,收集在《古史辨》七大冊中將近三百五十篇論文對上古史研究是否有建樹,在哪些方面值得采信,是古史研究工作者特別感興趣的。但這個運動何以會爆發,以什么樣的風貌出現,帶來什么影響,則是關心近代思想史的人所該處理的,二者固然有交集之處,但卻不可混為一談。在描述歷史現象時,是有必要對“心理事實”(psychological truth)與“歷史事實”(historical truth)加以分殊的。不管合理或不合理的思想都可能在歷史上造成巨大的影響,在行動者自己看來也都可能自認為掌握了最完整的理由,而且也正好符合著某種深刻的社會需求,而又造成了無可抹殺的歷史事實。我們在這個研究中尤其覺察到此點。在本書中筆者還希望注意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思想家原來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這些想法與他生活于其間的思想傳統有什么樣的關系?第二個層面是,他真正做到了什么?有時候所思所想與實際做成的結果之間有著相當遙遠的距離。第三個層面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所做成的產生了什么影響,這包括后來的人怎樣去理解他的作為。事實上,后來者的理解也常常跟作者的本意相沖突,被影響的人常常反過來與影響他的人在某些層面上形成敵對。為了照顧到這三個層面,本書的詳略遂與前人的研究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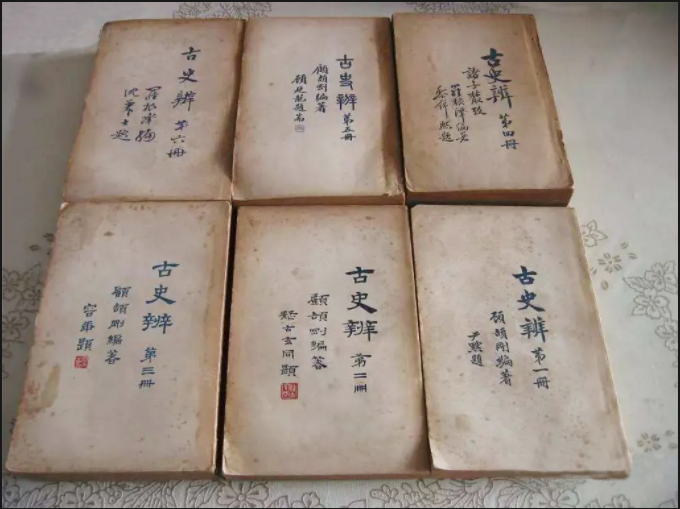
《古史辨》書影
截至目前,對古史辨進行比較全面性探討的著作并不算多。在外文著作中,施耐德(LaurenceA.Schneider)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算是先鋒之作。此書主要是顧氏一生學術思想的總說,而不是以古史辨運動為主要論題。它的優點是使我們能夠較完整地掌握顧氏一生學術研究的各個不同階段所展現之風貌。德國的吳素樂(Ursula Richter-Chang)女士以古史辨及顧頡剛為學位論文,其書尚未面世,故內容不得而詳。氏曾于1980、1982年兩度前往北京,對顧氏生平傳記資料作過相當深入的搜理。據我個人所知,中文著作中也只有不到十篇論文,因客觀環境的限制,故得以寓目者亦僅及其半。其中童書業、楊向奎、李錦全的論文大抵是站在批判古史辨派研究成果之立場而撰寫的,并不是純粹的學術思想史研究。尤其是童、楊二位的文章,皆發表于1952年,彼時批判胡適集團的運動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而顧頡剛正是被當作胡適集團的一員要將來看待的,所以即使是顧氏從檢字廠工人一手識拔栽培、又親身參與《古史辨》第7冊編輯工作的童書業,也對以顧氏為主干的古史辨派作了極為嚴厲的攻擊。
童氏指出:所謂古史辨派其實“是美國實驗主義傳到中國后的產物”,他自省道:“我們講了幾十年的古史,編著了厚厚的許多冊書,除起了些消極的破壞作用外,對于古史的真相何嘗摸著邊際……‘破壞偽古史就是建設真古史’,這句話未免太不著實了罷。”他的文章中宣稱要“在唯物辯證法這面寶鏡照臨之下,我們可以去偽存真,化無用為有用:這才是研究中國古史最正當的方法;對古史傳說一味抹煞,決不是科學的態度”。楊向奎也是古史辨運動中的一員要將,不過在當時他與張蔭麟、錢穆等皆持較保守觀點。他在《“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這篇短文中,很直接地指出顧頡剛“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學家”。他又指責古史辨派凡是遇著弄不清楚的古代史問題,就說是后人的偽造,是武斷的主觀論者,尤其對顧氏提倡的“層累造成說”,更施以極不客氣的攻擊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根本不能成立,這不是層累地造成。后人不可能‘造’古代史,根據一定的傳說或記載而有所整理是有的,但這不是造成。”楊氏后來又依據這一篇文章大幅修改成《論“古史辨派”》一文,這次改削最大的特點是他轉而承認古史辨的一些正面價值。

錢穆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李錦全的《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寫于1956年,是一篇比較詳細的批判文字。他指出古史辨派疑古論之所以錯誤,是由于他們拿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來代替歷史,認為這些具有神話色彩的人物是后人偽造的,是無法證實的,因此否認神話傳說中仍可能有某種歷史真實性。他認為在古史辨派的作品中,古史的命運是被神話傳說中人物的命運所決定的,由于這些傳說人物不可信,就宣稱上古史沒有實際證據。他與童書業一樣,把這些缺失歸結到“是由于他們用唯心觀點看問題,以為歷史可以由人隨口編造的結果”,他也同樣把解決上古史的契機放在唯物史觀上。
童、楊、李三位的論文主要是站在批判胡適集團的觀點而寫的,所以批判遠多于分析,事實上較難讓人們對這一個疑古運動的來龍去脈增加了解。故可說直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專篇針對古史辨運動的思想史背景加以比較全面而深入的檢討。本書便是想在這一個點上略獻綿薄,故本書的著重點與前人不盡相同,所詳所略亦有殊。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比喻,如果古史辨是一場大火,我個人特別想追問的是造成這場漫天大火的火藥。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興起,都有無法窮舉的背景,而且其中可能沒有一件會再度發生,但是毫無疑問的,在諸多因素之中,卻有著主從輕重之別。韋伯曾用一個“假說分析”(hypothetical analysis)的模型來鑒別“特定因素”(the factor)—亦即是說在研究人類事務時,某些因素被去除時,會在一個既定的事件系列當中,造成決定性的差異。本書主要是探討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的重要因果關聯。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雖然不是促成古史辨運動的唯一因素,但卻很具關鍵性。事實上,巨大的歷史事件就像任何一個巨大的海浪一樣,都是匯集無數潛流而成,故歷史單因論是很難被接受的,可是要窮舉所有的因果關聯也絕對做不到。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只能大致做到分別主從輕重,并把最具關鍵性的因素厘清出來。本文選取了這類關鍵因素中的一個來進行比較詳細的探討,并不意味著其他因素都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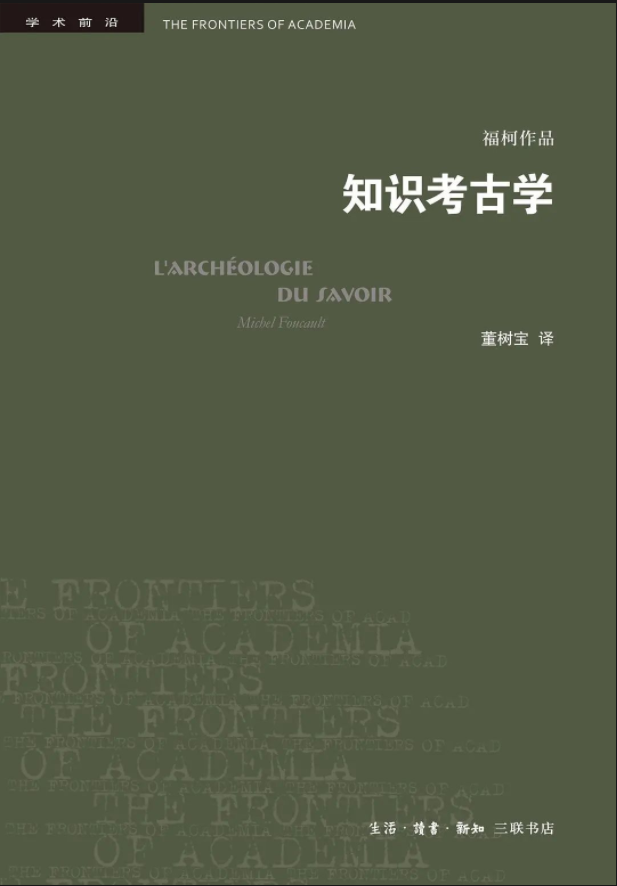
《知識考古學》
一接觸到所謂思想史背景時,便不能不聯想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對思想史所處理的“延續性”作相當嚴厲的攻擊。但筆者覺得思想史中的某些論題確具有因內在長期對話所構成之延續性。這使人們想到法國年鑒學派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對歷史時間所作的三種劃分:一種是結構性的,也就是長程時間(longduration),這主要討論人類生活中一些改變緩慢,延續數世紀或更久的結構。另一種是中程時間,他稱之為“時期”(conjunctures),十年或一代才會變化。第三種是“事件”(events),他又稱之為短程時間(short time span)。布羅代爾主要是運用這三種時間來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問題。個人認為,這三種時間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全部),也給予思想史研究相當的啟示。試著考慮思想史中的一些長程因素,使得我們稍稍能夠了解,為什么一些兩千年以上的舊問題,會在晚清被爭論得津津有味,而又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的古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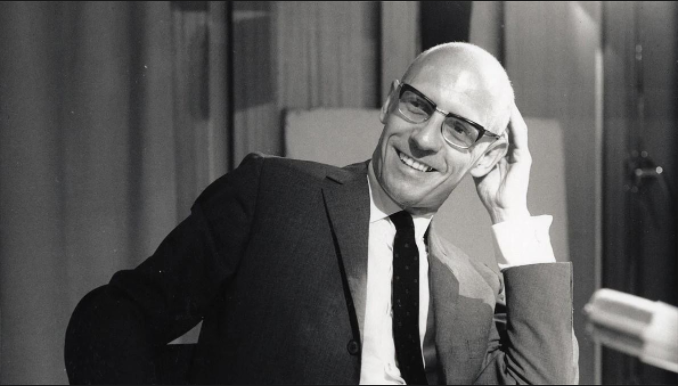
福柯
以本書為例,不管是全盤否定古文經,或將今文經寓言化,都有中國思想史內部長遠發展的背景為基礎(但這并不是暗示長程發展的結果必然會誕生古史辨運動),如果沒有這些長遠的因素,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主要論題很可能就屬于別的范疇了。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不是近代中國外在環境與思想學術錯綜復雜的變化,那么即使有著今古文經長期的糾斗,或許也根本不可能爆發出像古史辨這樣的運動。深入一點追究,我們甚至還可以說,如果沒有顧頡剛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進行沖天一擊,古史辨運動是否可能爆發也在未定之天。今古文之爭、清末民初的環境、顧頡剛個人的因素三者正好同時說明了長程、中程、短程因素的重要性。也正因想同時照顧到這三種時間,所以本書花費許多篇幅在追溯問題的產生及長遠的脈絡上。這主要是想解答:為何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變化仍然纏繞在那些古老的問題上。但是強調長期發展的內在脈絡并不是要宣揚歷史有所謂的“不可避免性”。事實上在這本書中,筆者也強調長期蘊蓄的力量如果沒有得到重大的觸緣,并不一定會爆發出來。如果以博弈為例,有利于某歷史事件的長遠背景正如同拿到一副好牌,可是如何獲致勝算,在相當程度上仍由游戲者個人的技術與當時的運氣來決定。所以是長遠的背景與當事的個人交互作用,而不是某方完全決定另一方。
本書第二章的一小部分及第三章,曾經以《激烈的托古改制論對古代信史造成的破壞》為題,于1986年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召開的“中國經世思想史討論會”中宣讀,并得到一些有益的批評。筆者之所以在討論經世思想時報告這個論題,是因為感于知識分子在解釋經典時,常為了經世的要求,刻意與時代尋求關聯,竟至嚴重扭曲歷史的客觀性。誠如大家所周知的:中國思想史中有很長遠的經世傳統,而“通經致用”是這個傳統中相當有力量的一支。但是,在“通經致用”的目標下常會碰到這樣一個困難—如何把已經定型的經典運用到每一個時代不同的特殊境況上,既要照顧到訊息的完整性,同時又要照顧到境況的特殊性。成功的經典解釋者應當一方面守著經典,一方面關照他的時代,故經典與境況二者應該相互關聯呼應(correlate),而不是相近似(similar),它們之間永遠存在一種緊張—到底門要決定房屋的結構到什么程度?或房屋該決定門到什么程度?想在這一工作上掌握一個恰當的分際并不容易。
如果不能把握住恰當的分際,便常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為了使經典所啟示的訊息與現實境況更密切相關,解釋者自覺或不自覺地依照自己的意見來支配經典。換句話說,就是“在死人身上玩詭計”(ingenious trick played on the dead),強古人以就我的結果,是使經典淪為個人的思想服務之工具。

康有為
所以在那次報告中,個人主要是討論:在晚清的變局中,廖平、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了變法改制,對經書所作的種種新解,及這些工作所造成的“本意尊圣、乃至疑經”的吊詭性結果。不管是廖平、康有為或梁啟超,他們對經書(尤其是《春秋經》)的種種新解釋,大抵圍繞著四個核心:(一)他們希望強化孔子的權威,并將孔子的形象由古文家所認定的史學者變成為政治社會改革者,也就是不再把孔子當成一個單純的歷史文獻整理者,而是當作一個提倡經世變法的改革家。(二)由于他們所形塑的孔子是一個沒有實際職位的社會政治改革者,所以《六經》不再只是單純的歷史文獻,而是孔子寄托其經世計劃的書,其中最激烈的一種看法是把經書中所記載的歷史和真正的上古歷史分為兩層,甚至將史事當成符號看。(三)他們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希望透過以《六經》為依據的托古改制,寄托其變法思想,故往往把自己的思想緣附到經書上。(四)為了使孔學能在現代社會中保有尊位,他們把孔子解釋成全知全能的圣人,其思想可以范圍萬世,《六經》乃搖身一變為預言書。不管是將經書中的史事徹底符號化,或將之變成預言書,都不期然地把經書中所記載的古代信史一筆抹殺了。
這個討論主要是想說明一個相當普通的歷史現象:不管從事歷史敘述或經典解釋,最大的一個忌諱是強古人以就我,或甚至是為了寄托一己的經世思想而把經史之學弄成影射之學。如果這樣,不但失去了我們學習經史的意義,同時還潛藏著嚴重的危機。余英時教授在談到“文革”“影射史學”為了達到史學為政治服務的目的而不惜犧牲歷史客觀性時說:“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又是和政治任務的迫切性成比例的。當任務最迫切的時候,史學上的一切求知的戒律都將被棄置不顧了。”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本書第二、三章便同時想凸顯經典解釋與現實致用間的緊張性。
筆者之所以敢于將此書付梓,并不是相信這個研究工作已經完成。事實上沒有一篇研究文字有完成的一天的。任何研究文字永遠都應該再修再改,再補再削,可是個人在情感上卻很愿意將它告一段落,才好專心致力于分內的其他工作。
本書撰寫過程中,承張灝先生、余國藩先生惠示寶貴意見,業師李永熾先生、鄭欽仁先生,及黃進興、沈松僑、廖棟梁、彭明輝、王健文等兄閱讀原稿,謹此致謝。此外,直接或間接給我關懷與鼓勵的人還很多,可惜無法在此一一致意。本書出版過程中,多承允晨出版公司負責人吳東升兄及時報出版公司的雅意,謹此致謝。
王汎森謹識于南港
1987年1月
(本文選自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修訂版)》,世紀文景2024年7月出版,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