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看了幾遍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后,我又認真閱讀了斯蒂芬金的小說。本文內容主要參考了小說。
肖申克既是監獄,也是人生的象征和社會的隱喻,這一點,作者借故事的講述者瑞德明確表示:
“我把監獄描繪成外面社會的縮影”。
那么,肖申克所隱喻的社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處處體制化的社會。
1
“體制”可理解為包括某種規則、習慣、意識和氛圍的環境,體制化通常指一種按部就班的生活,人們生活在其間,只能按照固定的模式行事,起初只是一種外在約束,慢慢地人們適應這種約束,最后人們離不開這種約束。體制化意味著對權威的服從,對自由的排斥。
根據百度百科釋義,因為人對一種事物的依賴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維以及習慣,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外后,人們本能的反應是想在新的體制內尋找舊的體制拘束。就和一個方形在大的方形內可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處,但如果大的環境變成了圓形,那么方形就開始以自己的形態去配合圓形,這是不可能的事,而最終方形會心身力竭,悲劇就會這樣的發生。
但如果方形將自己的容積變大,或者變小,它未必在圓形內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處,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就會形成一種習慣性,而這種習慣性就是體制化。
體制化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社會的產物,它的根源是意識形態。
2
體制化作為社會產物,如何使個體體制化呢?小說中瑞德的一段獨白做了形象描述:
“我曾經試圖描述過,逐漸為監獄體制所制約是什么樣的情況。起先,你無法忍受被四面墻困住的感覺,然后你逐漸可以忍受這種生活,進而接受這種生活……接下來,當你的身心都逐漸調整適應后,你甚至開始喜歡這種生活了、什么時候可以吃飯,什么時候可以寫信,什么時候可以抽煙,全都規定得好好的。
如果你在洗衣房或車牌工廠工作,每個小時可以有五分鐘的時間上廁所,而且每個人輪流去廁所的時間都是排定的。三十五年來,我上廁所的時間是每當分針走到二十五的時候,經過三十五年后,我只有在那個時間才會想上廁所:每小時整點過后二十五分。如果我當時因為什么原因沒辦法上廁所,那么過了五分鐘后,我的尿意或便意就會消失,直到下個鐘頭時鐘的分針再度指在二十五分時,才會想上廁所。”
這段描述雖有帶有文學夸張,卻也直擊體制化的核心。它表明體制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漫長的馴化過程。人一旦被體制化,就近乎本能地過上循規蹈矩的生活,不敢質疑批判,不敢越雷池半步。體制化的個體一旦被拋入一個陌生的環境,就變得格格不入。我們從瑞德假釋后適應新世界的過程,就能看到體制化根深蒂固的影響:
“我一時之間很難適應這一切,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適應,就拿女人來說吧。近四十年的牢獄生涯,我幾乎已經忘記女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突然之間,我工作的地方充滿了女人——老女人、懷孕的女人(T恤上有個箭頭往下指著肚子,一行大字寫著:‘小寶寶在這兒’),以及骨瘦如柴不穿胸罩、乳頭隱隱凸出的女人(在我入獄服刑之前,女人如果像這樣穿著打扮,會被當街逮捕,以為她是神經病)等形形色色的女人,我發現自己走在街上常常忍不住起生理反應,只有在心里暗暗詛咒自己是臟老頭。
上廁所是另一件我不能適應的事。當我想上廁所的時候(而且我每次都是在整點過后二十五分想上廁所),我老是有一股強烈的沖動,想去請求上司準我上廁所,我每次都忍得很辛苦才沒有這么做,心里曉得在這個光明的外面世界里,想上廁所的話,隨時都可以去。關在牢中多年后,每次上廁所都要先向離得最近的警衛報告,一旦疏忽就要關兩天禁閉,因此出獄后,盡管知道不必再事事報告,但心里知道是一回事,要完全適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假釋后明明獲得了自由,瑞德卻在很長時間連上廁所都會習慣性地請求上司準許,這正是體制化的一大危害:當體制強加的東西消失后,它們依然在你身上陰魂不散。小說中提到的波頓和他的鴿子“杰克”,也是被體制附身的典型。瑞德講到:
“我認識一個叫波頓的家伙,他在牢房里養了一只鴿子。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當他們放他出來走走時,他都帶著這只鴿子。他叫鴿子‘杰克’。
波頓在出獄前一天,也放杰克自由,杰克立刻姿態漂亮地飛走了。但是在波頓離開我們這個快樂小家庭一個星期之后,有個朋友把我帶到運動場角落,波頓過去老愛在那里晃來晃去。有只小鳥像一堆臟床單般軟趴趴地癱在那里,看起來餓壞了。我的朋友說:‘那是不是杰克啊?’沒錯,是杰克,那只鴿子像糞土一樣躺在那兒。”
透過波頓的小鳥,我們可以發現,所謂體制化,就是一個牢籠,長期生活在牢籠中,人的本能極大地退化,一旦被放到一個自由的環境中,就變得無所適從,最終不免被世界所淘汰。這種現象并非個例,它具有普遍性。
3
之前有位高鐵列車員被開除后,撒潑式地哭訴:“自己年齡太大了,除了高鐵列車員的工作,什么也干不了。”說明她也被體制化了。其實,何止某些人,我們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被體制化了,只是有的人中毒太深,以致于完全不能適應體制外的世界;有的人體制化的程度輕一點,所以即使離開了舊體制,也能慢慢適應新體制。
小說還講到布魯克的遭遇,他也是典型的體制化的受害者。
“布魯克是在柯立芝還在當總統的時候,賭輸后失手殺了妻女而被關進來。他在一九五二年獲得假釋。像往常一樣,政府絕不會在他還對社會有一點用處的時候放他出去。當罹患關節炎的布魯克穿著波蘭西裝和法國皮鞋,蹣跚步出肖申克大門時,已經六十八歲高齡了。他一手拿著假釋文件,一手拿著灰狗長途汽車車票,邊走邊哭。
幾十年來,肖申克已經變成他的整個世界,在布魯克眼中,墻外的世界實在太可怕了、就好像迷信的十五世紀水手面對著大西洋時一樣害怕。
在獄中,布魯克是個重要人物,他是圖書館管理員,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果他到外面的圖書館求職的話,不要說圖書館不會用他,他很可能連借書證都申請不到。我聽說他在一九五三年死于貧苦老人之家,比我估計的還多撐了半年。是呀,政府還蠻會報仇的:他們把他訓練得習慣了這個糞坑之后,又把他扔了出去。”
幾十年的監獄生活,布魯克早已習慣了周遭的一切,不僅意識不到體制化的危害,還喜歡上了這種生活,因為在這里,他存在感十足,而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就變得一無是處。
瑞德也有這種感受,當安迪希望他出獄后為他搞定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一切時,他感到自己根本沒法勝任。
“我沉吟良久,當時我想到的最大困難,居然不是我們不過是在監獄的小運動場上癡人說夢,還有武裝警衛居高臨下監視著我們。‘我沒辦法:我說,我無法適應外面的世界。我已經變成所謂體制化的人了。在這兒我是那個可以替你弄到東西的人,出去以后,如果你要海報、錘子或什么特別的唱片,只需查工商分類電話簿就可以。在這里,我就是他媽的工商分類電話簿,出去了以后,我不知道從何開始,或如何開始。”
瑞德其實不像他想得這么糟糕,他走出監獄依然可以適應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但是,對不確定世界的過分恐懼束縛住了他的想象。
4
在長久的體制化后,對于那些總是嘗試越獄(也就是極力沖破體制牢籠)的犯人又怎樣呢?多半也在劫難逃,因為奴在心者,身上枷鎖去掉后,依然跑得過和尚跑不了廟。這也正是體制化最可怕之處。瑞德對肖申克中這種現象洞若觀火:
“……比較認真策劃的越獄行動大概只有六十件,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的‘大逃亡’,那是我入獄前一年發生的事情。當時肖申克正在蓋新的行政大樓,有十四名囚犯從沒有鎖好的倉庫中拿了施工的工具,越獄逃跑。整個緬因州南部都因為這十四個‘頑強的罪犯’陷入恐慌,但其實這十四個人大都嚇得半死,完全不知該往哪兒逃,就好像誤闖公路的野兔,被迎面而來的大卡車車頭燈一照,就動彈不得。結果,十四個犯人沒有一個真正逃脫,有兩個人被槍射死——但他們是死在老百姓的槍下,而不是被警官或監獄警衛逮著,沒有一個人成功逃脫。
從一九三八年我入獄以來,到安迪第一次和我提到齊華坦尼荷那天為止,究竟有多少人逃離肖申克?把我和韓利聽說的加起來,大概十個左右只有十個人徹徹底底逃脫了。雖然我沒有辦法確定,但是我猜十個人當中至少有五個人目前在其他監獄服刑。因為一個人的確會受到監獄環境制約,當你剝奪了某人的自由、教他如何在牢里生存后,他似乎就失去了多面思考的能力,變得好像我剛剛提到的野免,看著迎面而來、快撞上它的卡車燈光,卻僵在那里動彈不得。”
這些越獄的犯人以為逃出了肖申克就能獲得自由,殊不知,在喪失了追求自由的能力后,在飛翔的翅膀被折斷后,所謂跳出牢籠,不過是跳出一個牢籠又鉆進另一個牢籠。
5
但是,人真的注定要被體制馴服嗎?在肖申克監獄中,安迪正是那個從始至終未被馴化的人,他是真正“單純”的自由人。他就是那種注定要飛翔的鳥兒,正如瑞德的獨白:
“有些鳥兒天生就是關不住的,它們的羽毛太鮮明,歌聲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們走,否則哪天你打開籠子喂它們時,它們也會想辦法揚長而去。”
當然,安迪·杜佛尼的自由之路并不容易,體制的牢籠給他的自由設置了重重障礙,“姊妹”的暴力騷擾、動輒得咎的禁閉、虛偽而蠻橫的典獄長的專制、越獄時惡劣的管道……每一個障礙都可能致人死地或讓人永不得翻身。但他從不曾屈服,二十七年的牢獄生活沒有磨平他渴望自由和救贖的棱角,他的十英尺長的鶴嘴鋤石錘始終在挖體制化的銅墻鐵壁。在瑞德看來要六百年才能挖通地道,而安迪用二十七年(雖然也漫長)就越獄了。
尼采說“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何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種生活”,安迪正是這種為了心中的希望和自由而甘愿忍辱負重的人。
肖申克的監獄監禁了他的身體,卻沒有打垮他的希望和勇氣。正如安迪所說:“世上有些地方,石墻是關不住的。在人的內心,有他們管不到的地方是完全屬于你的。”安迪始終保持著未被體制化的清醒,最終實現了自我救贖。所以就算他最后越獄失敗,也是當之無愧的勇士。
最后借電影中安迪的一段告白,與大家共勉:
“如果你感到痛苦和不自由,我希望你心里有一團永不熄滅的火焰,不要麻木,不要被同化,拼命成為一個有力量破釜沉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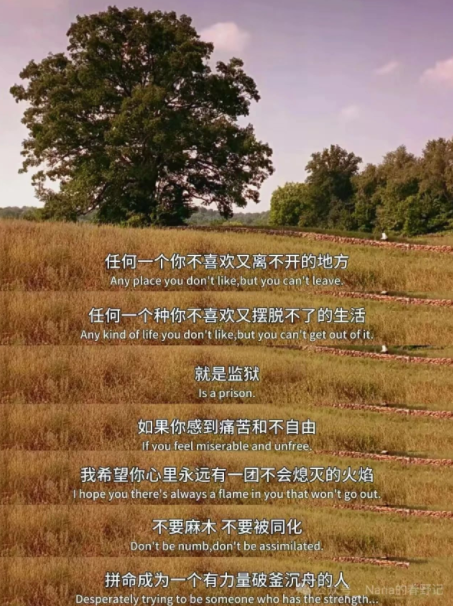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讀書人的精神家園。轉載僅供學習交流,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